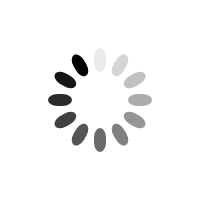文学
类型
8.3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205千字
字数
2021-12-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讲述炽烈的爱情和死亡,在对人生片刻的描写中把握时代全貌。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和《故事集》三个部分,它们展现了作为“世界一百位最佳小说家”之首的巴别尔的精华之作。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与素材有两大来源,一是军队战斗生活和一个个具有鲜明性格的军中人物,二是作者故乡敖德萨的众多人物(也包括作者自己),特别是底层和贫困民众及其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
巴别尔善于捕捉强烈、生动的细节,以一个具体的动作、事件或汇集众多戏剧性要素的画面,来展现复杂的社会面貌、不同群体相互较量的势能和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目录
- 版权信息
- 导读 非常的小说,非常的小说家
- 译者前言 任何诋毁攻击都无法消灭真正的艺术
- 伊·埃·巴别尔
- 自传
- 红色骑兵军
- 横渡兹布鲁奇河
- 新城的天主教堂
- 家信
- 军马储备局局长
- 阿波列克先生
- 意大利的太阳
- 格达利
- 我的第一只鹅
- 拉比
- 通往布罗德之路
- 闲话敞篷马车
- 多尔古绍夫之死
- 第二旅旅长
- 萨什卡基督
- 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传
- 科津墓地
- 普里谢帕
- 一匹马的故事
- 休息地
- 别列斯捷奇科
- 盐
- 傍晩
- 阿丰卡·比达
- 在圣徒瓦连特圣骨匣旁
- 骑兵连长特鲁诺夫
- 两个伊万
- 续一匹马的故事
- 寡妇
- 扎莫希奇
- 叛变
- 切斯尼基村
- 战斗之后
- 歌曲
- 拉比之子
- 阿尔加马克
- 吻
- 敖德萨的故事
- 国王
- 在敖德萨这是怎样发生的
- 父亲
- 柳布卡哥萨克
- 我的鸽子窝的故事——献给马·高尔基
- 初恋
- 你错了,船长!
- 养老院的末日
- 卡尔-扬克利
- 在地下室里
- 觉醒
- 迪·格拉索
- 弗罗伊姆·格拉奇
- 故事集
- 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加丽塔·普罗科菲耶夫娜
- 妈妈,里玛和阿拉
- 兴奋
- 沙博斯-纳赫穆
- 卡莫号和邵武勉号
- 在女皇王宫度过的一晚
- 耶稣的罪过
- 圣伊帕季的末日
- 线条和色彩
- 道路
- 居伊·德·莫泊桑
- 石油
- 但丁大街
- 审判
- 答复
- 蝴蝶花号轮船
- 苏拉克
展开全部
出版方
世纪文景
2002年6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其分支出版机构世纪文景,全称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文景致力于立足“社科新知、文艺新潮”,阅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