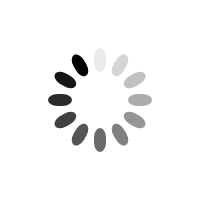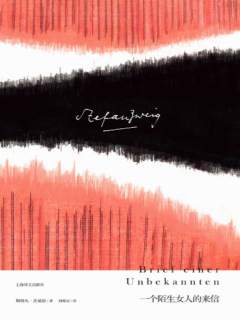文学
类型
8.7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153千字
字数
2016-10-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本书享誉世界的作家茨威格中短篇小说精华。茨威格擅长抒写心灵和情绪的激荡,被誉为“打开弗洛伊德危险闸门的心灵猎手”
内容简介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集,收录8篇,其中包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等名篇。其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最广为人知,曾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和舞台剧。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没有署名和地址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也就是收信的男人对此一无所知。故事始自18年前,她初遇男人的刹那,她还是个孩子,而后经历了少女的痴迷、青春的激情,甚而流落风尘,但未曾改变对男人的爱,直至临死前才决定告白——她躺在凄凉的命运的甲板上,雪白的泡沫把她推向了虚无……
目录
- 版权信息
- 普拉特的春天
- 忘却的梦
- 家庭女教师
- 朦胧夜的故事
- 灼人的秘密
- 伙伴
- 神速的友谊
- 三重唱
- 进攻
- 大象
- 前哨战
- 灼人的秘密
- 沉默
- 撒谎者
- 月光中的踪迹
- 袭击
- 暴风雨
- 初步领悟
- 纷扰的晦暝
- 最后的梦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夏天的故事
- 桎梏
展开全部
出版方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1月,系世纪出版集团的成员。上海译文出版社以译介和传播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主要任务,拥有众多精通英、法、俄、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主要语种并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的资深编辑;其强大的译作者队伍中多为在外语和中文方面学有专长、造诣精湛的专家学者;该社同各国主要的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有着广泛、持久的联系,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领域信誉卓著。三十多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翻译、编纂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双语词典和外语教学参考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