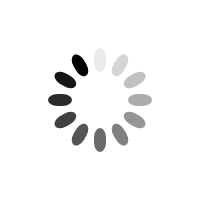文学
类型
9.2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402千字
字数
2014-06-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译文经典,个人必藏。揭露出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内容简介
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起初他觉得“杀死这百无一用、象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后来受到“良心”谴责。他遇到醉汉马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感到了拉斯柯尼科夫。于是他去官府自首,并走向“新生”。
2.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184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受到高度评价。1848年发表中篇小说《白夜》。1849年因参加反农奴制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此期间发表有长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
目录
- 版权信息
- 译本序
- 第一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第二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第三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第四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第五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六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尾声
- 一
- 二
展开全部
出版方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1月,系世纪出版集团的成员。上海译文出版社以译介和传播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主要任务,拥有众多精通英、法、俄、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主要语种并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的资深编辑;其强大的译作者队伍中多为在外语和中文方面学有专长、造诣精湛的专家学者;该社同各国主要的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有着广泛、持久的联系,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领域信誉卓著。三十多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翻译、编纂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双语词典和外语教学参考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