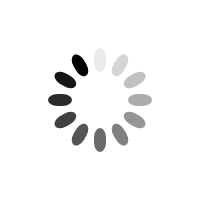小说
类型
8.1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60千字
字数
2005-07-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译文经典,个人必藏。杜拉斯名作。面对深沉无望的爱情,宣言“爱情于我就是不死的欲望”。
内容简介
以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贫穷的法国女孩与富有的中国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自从这个男人牵起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悲剧……
目录
- 版权信息
- 情人
- 翻译后记
展开全部
出版方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1月,系世纪出版集团的成员。上海译文出版社以译介和传播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主要任务,拥有众多精通英、法、俄、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主要语种并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的资深编辑;其强大的译作者队伍中多为在外语和中文方面学有专长、造诣精湛的专家学者;该社同各国主要的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有着广泛、持久的联系,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领域信誉卓著。三十多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翻译、编纂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双语词典和外语教学参考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