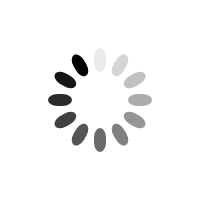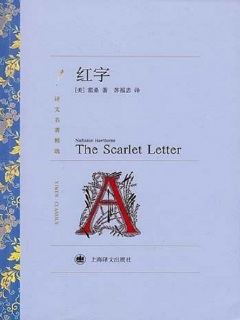小说
类型
7.8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173千字
字数
2011-01-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杯,层层深入地探究了罪恶和人性的各种道德、哲理问题,全书以监狱和蔷薇开场,以墓地结束,充满丰富的象征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精美木刻插图近三十幅,极具收藏价值。霍桑的《红字》是浪漫主义作品,写爱情和婚姻,理所当然,却又不大容易用一般的道理来评述,因为正面的爱情和婚姻描写,整部作品里几乎不存在,这是所有读过《红字》的读者都难免有的疑问。
目录
- 版权信息
- 译本序
- 第二版 前言
- 海关——《红字》的前言
- 一 牢狱门口
- 二 市场
- 三 认出
- 四 会见
- 五 赫斯特做针线
- 六 波儿
- 七 总督的过厅
- 八 机灵的孩子与牧师
- 九 医生
- 十 医生和他的病人
- 十一 心的深处
- 十二 牧师的守夜活动
- 十三 赫斯特的另一种视角
- 十四 赫斯特和医生
- 十五 赫斯特和波儿
- 十六 林中散步
- 十七 教区牧师和教区居民
- 十八 一片阳光
- 十九 小溪旁的孩子
- 二十 迷惑中的牧师
- 二十一 新英格兰的节日
- 二十二 游行
- 二十三 红字的暴露
- 二十四 尾声
展开全部
出版方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1月,系世纪出版集团的成员。上海译文出版社以译介和传播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主要任务,拥有众多精通英、法、俄、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主要语种并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的资深编辑;其强大的译作者队伍中多为在外语和中文方面学有专长、造诣精湛的专家学者;该社同各国主要的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有着广泛、持久的联系,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领域信誉卓著。三十多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翻译、编纂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双语词典和外语教学参考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