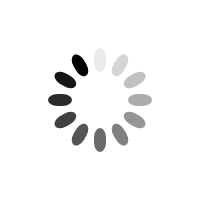主编推荐语
阿乙、颜歌、双雪涛、文珍、李静睿、李娟、邹波、刘子超、云也退……《单读》视野中最好的一批青年作家,首次集体发声。
内容简介
“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穆旦
经常有人使用“黄金时代”的提法,有的人是真心这么认为,而有的人是持有反讽之意。这次《单读》在当下的情形之下,重提这个概念,则是出于我们对于“黄金时代”的另一重理解——在焦虑之际保持清醒,在沉默之时尝试发声,在混乱之地继续潜行,既然我们遭遇的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去拥抱变革,既然所有人都说可能性已经几乎穷尽,那我们就偏要试试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既然我们周围仍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热爱写作、阅读和思考,那么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呢?尤其,我们不再期待谁的奖赏,甚至不期待鼓励,我们等待迎接批评、讽刺和漠视。因为,如果我们一再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迷路,那么唯有站在现在的泥土中,重新举起希望的火炬,是时候从悲观中清醒,让写作重新振奋起来。
目录
- 版权信息
- 文学致幻剂
- 王德威专访 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
- 小说
- 世上没有鬼
- 平乐事
- 风后面是风
- 盐井风筝
- 跷跷板
- 诗歌
- 致未婚夫
- 影像
- 豫东和陇西
- 随笔
- 我的游荡
- 东京宝贝
- 伞兵
- 世间已无贝内特
- 翻译无易事
- 报道
- 词语
- 评论
- 波拉尼奥镇魂曲
- 穆旦 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
- 全球书情 特朗普、移民和反智主义的世界
- 撰稿人
出版方
单读
《单读》是单向空间的品牌出版物,它团结着新一代作者和读者,内容以小说、诗歌、文化评论、思想随笔、非虚构报道和艺术作品为主,推崇沉静、深入、优雅的阅读,尊重清醒、独特、富有活力的声音,致力于成为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 《单读》用全新的视角和文体看世界。我们如此强调文体,因为语言是思维的花朵,语言改变了,思维就改变了。 我们珍视作家和读者,特别是拥有全球化视野且兼具新鲜趣味的知识分子,以及思维独立、善于表达的新一代年轻人。我们推崇沉静、深入、优雅的阅读,尊重清醒、独特、富有活力的声音,在精神世界,《单读》要做不跟随的引领者,思考、记录、审美,将更多年轻人重新引导进入到书籍、艺术与思想的世界中,体验“思维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