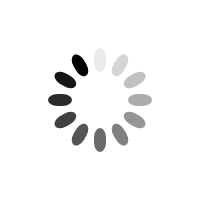历史
类型
7.9
豆瓣评分
可以朗读
语音朗读
178千字
字数
2019-01-01
发行日期
展开全部
主编推荐语
从靖康之变到绍兴内禅,带你重回那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幽深的岁月。
内容简介
近年来,由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南宋史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而建炎、绍兴之际南渡君臣的所作所为,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很值得深入研究。本书为著名宋史研究专家虞云国先生多面向探析宋高宗时代的一部力作。内容涉及靖康之变北宋王朝刹那覆灭到建炎南渡高宗政权初步立足的历史过程、宋高宗于岳飞在宋金和战上特殊的君臣关系等,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不仅代表了作者对于南宋初四十年历史的认识,更有助于一般读者深入认识“中国转向内在”这一主题。
目录
- 版权信息
- 鸣谢
- 自序
- 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
- 从靖康之变到建炎南渡
- 苗刘之变的再评价
- 莫道西线无战事
- 刘豫与杨么
- 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四重奏
- 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
- 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 宋代第二次削兵权
- 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读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 张俊供奉的御筵菜单
- 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读蔡涵墨《历史的严妆》
- 从绍兴更化到绍兴内禅
- 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重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两代君主同堂时
- “中兴圣主”与《中兴瑞应图赞》
- 中国为何转向内在——读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
- 附录:纪事年表
展开全部
出版方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全国著名综合出版社之一,主要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政治、法律、财经、管理、历史等学术专著和大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