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
世界各地夜间的人工照明,导致光污染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了 Globe at Night 项目过去十余年(从 2011 年到 2022 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夜空亮度平均每年增加了 10%,即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这一增长远远高于此前根据国防气象卫星计划和苏奥米国家极地轨道伙伴卫星估测的结果(每年 2%)—— 这些卫星无法检测到 LED 发出的蓝光,而 LED 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用于户外照明。夜间人工照明会干扰夜间褪黑素的产生,从而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光污染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生产、安装和操作户外人工照明设施会带来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户外照明大概需要 400 太瓦时的电能,预计产生 2000 亿公斤的二氧化碳。
1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16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看世界活泼不用太远,我就能找到乐子。西柏林最浮华的林荫道选帝侯大街的尽头提供了欧洲最活泼、最无拘无束的街景。在霓虹灯招牌的注视下,经过拥挤的路边咖啡馆,无穷无尽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从喧嚣的车流中涌过,哈哈大笑,昂首阔步,游手好闲,吃吃喝喝,演奏音乐,拥抱亲吻,炫耀卖弄,从下午短休时一直闹腾到黎明快结束。它像是一个永恒的集市,或者也许是一个杂货街市,斯文人和流氓扎堆,穷光蛋和阔佬混杂:带婴儿的吉卜赛乞丐,牵狗的布尔乔亚女士,餐厅饭桌旁拥抱的情侣,黑乎乎的门道里未刮胡子的外币贩子,灯光明亮的鞋店外演奏斯卡拉蒂的管乐三人组,在两棵树中间的一根绳子上不太熟练地走动的杂技演员,不知疲倦的鼓手,冗长乏味的哑剧,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冒出来的滑板少年,素描肖像画家,带便携式音响、鬼鬼祟祟蹲在自己制造的垃圾中间的年轻人,咖啡和新鲜面包卷的味道,街头滑过的双层巴士,水花泼溅的喷泉,人行道旁展示皮带和珠宝的玻璃橱窗 —— 统摄这一切、并被不协调地保留下来提醒我们勿忘旧时恐怖的,是丑陋的、坟墓般的威廉一世纪念教堂的残骸,它被泛光灯挑衅般地照亮。柏林人一直以其无法抑制的不敬与享乐主义而闻名,他们在任何压迫下都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即使在我第一次去那儿,它还是一座半毁的城市时就非常明显。在东柏林,与选帝侯大街相对应的是无情的亚历山大广场,即使在这边,在独裁统治已经倒台的今天,高昂的兴致也时常透过极权主义的坏脾气闪出光来。一位侍者眨巴眼,无视我们已经错过供应咖啡时间的管理规章。一个年轻人大胆地驾车以 V 字形路线掉头,在制动器和车轮打滑的尖啸声中,穿过卡尔・马克思大道去接他那位哈哈笑的女朋友。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那道墙,朝西的一边已经覆满壁画,并被称作 “东边画廊”。如今,柏林的空气中充满自由。在这儿生活很棒,在这儿做年轻人一定如在天堂。一切都在涌动,一切都在改变,新的地平线敞开,没什么强求绝对的尊敬或忠诚。尽管半个柏林是即将解散的民主德国理论上的总部,但这座城市实际上并非任何事物的总部,这赋予它一种不负责任的刺激感。实际上,娱乐的符号很多,但没有哪个比荒诞的小小的 “卫星” 牌轿车更可爱,它像是小精灵开的车,从东柏林蜂拥向西边,过夜生活,或者大采购,原始的引擎发出欢天喜地的哐啷声、呼哧声,每个车窗里都是笑脸。安逸走在米格尔湖旁的树林中,在一两年前会令人惊恐得无法形容的东柏林的一个角落里,我听到一段快活的德国旋律传来,嚯嚯、砰砰的音乐,一个热烈的男中音独唱,间或穿插着快乐的合唱。我沿着芦苇丛生的湖边(它远远的东岸上耸立着冷酷的黑色的工厂烟囱,那里曾经被叫作工人的天堂)跟着乐声穿过宁静的小路,尽管在我抵达音乐的源头之前,旋律已经变成了老汤姆・琼斯最爱的《绿草如茵的家》,但我仍然发现那场景有着典型的 “安逸闲适”—— 掺杂了伤感的家庭生活的舒适劲儿 —— 这是我的第二个柏林意象。我看到的第一个 T 恤衫口号是 “我做主”,印在一个家庭主妇丰满的胸脯上,当时她正和她那位显然毫不惧内的丈夫跳着充满活力的迪斯科快步舞。我正赶上东柏林的公共假日,在湖边的一个旅馆,几千个市民,从老祖母到抱在怀里的婴儿,正在阳光中享受家庭宴会。他们多么完美地满足了我的设想!他们多么愉快亲切地大笑、唱歌、跳舞、喝啤酒、吃腌猪蹄!两支乐队带着多么不知疲倦的微笑轮番献艺,一支奏起古老的嗡啪啪,另一支不断探索着不太嘈杂的摇滚!我望着他们,如此激情奔放,如此亲密热络,我意识到柏林的 “安逸闲适” 有着多么无穷的力量,它经历战争与和平、独裁与革命、希望与灾难,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在大杯啤酒和甜筒冰激凌之上绵延不断。它不知道什么边界,也不认得什么意识形态,就我自己而言,我发现它有一种略微叫人不安的品质,绝对能够让它漠视历史。我不信任它潜在的歧视倾向 —— 比如,针对西柏林无所不在的土耳其移民。我不喜欢它那些愚蠢的方面,明显地遍布于这座城市那些滑稽的雕像、暗藏机关的喷泉和相当沉闷的幽默中。不管是好是坏,柏林的安逸是它本身的一种气质,并且无可逃避。我们在史潘道区的一场简朴的婚礼上看到它,披着长长的白色婚纱的新娘,系着高高的白色硬领巾的新郎,牧师和亲切的祭坛少年,不停拌嘴的唱诗班女孩,孤零零、戴眼镜的女傧相(粉红色的眼镜很配她粉红色的衣服),穿得过分隆重的家族宾客,偶尔路过的人,甚至连我们在内,全都被拥抱在它的亲切和蔼中。我们在古耐沃德森林里一个露天餐厅观察到它,在两位中年女士身上,她俩一边吃芦笋一边咯咯笑,冲我们鼓励般地微笑、点头,小心翼翼地把手包在酒杯边沿放稳,避免栗子花落入杯中。不管是好是坏,柏林的安逸是它本身的一种气质,并且无可逃避。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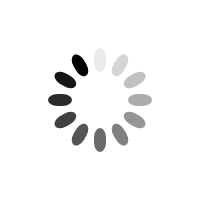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看世界(2023年03期)
本期重点文章《“备胎”王子复仇记》《末代希腊王之殇》《加州新年惨案说明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