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流民与流放
到 2022 年 7 月,英格玛・伯格曼去世 15 年了。15 年前,也就是 2007 年 7 月 30 日,伯格曼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惊呼,原来伯格曼还活着。也就是说,当人们把 [第七封印][野草莓][假面] 等作品供奉进神殿的时候,他一直隐居在法罗岛,默默地注视这个和他的电影已经完全迥异了的世界。不得不说,当我们把某些东西奉为神物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一事物高不可攀,暗示了可以用虚拟的敬意理所应当地远离它。这是一个非常伯格曼的场景,尤其是他放弃镜头而只用眼睛去拍摄的时候。伯格曼的作品太严肃了,一直在已经堪称精密的人类社会体系里挖掘人性的废墟,和这个嬉皮笑脸的当下已经格格不入了。伯格曼是电影史上第一位哲人,他的电影是意义纠缠之地。他对死亡、宗教、婚姻、谎言和真相的凝视,进而生出人之所以为人的诘问。他的人如一介流民,他的作品既锐且钝,既温又冷。伯格曼是极少数真正的死硬分子,他一生都没能学会和解。他一直在审视人,但他的电影不是审视他者,而是填塞着大量个人信息,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他把观众当人,他叩问人类灵魂的秘密,首先是不回避自己灵与肉的撕扯。伯格曼的电影里爬满了大段大段的自述式镜像,在 [第七封印] 里,他说 “我一生都在寻找,希望能够没有意图和利害关系的交谈,一无所获。我这样说,没有苦闷和自责的意思,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如此。” 伯格曼对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如血缘关系中对峙的父子,如法律关系中互相折磨的婚姻,都布满了近乎于冷酷的沉静。在他的电影里到处都是对人这一物种兽性与人性杂处的困惑以及人与人关系不可解的感喟,他的诘问漫长得如同一声叹息。他在电影里述说了无数次的生死,真的在现实中发作时,也是以一种超逻辑的视角出现。在群氓狂欢的鼓声里,冷眼旁观,享用孤独,在某一天掷杯为号,用死亡宣告了还活着。他的热爱是痛苦制作的,他的上帝视角是以不惜质疑上帝的方式出现的。伯格曼不聚焦宏大,只是一次次地将镜头深入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他在这些瞬间里发现了永恒。他在生活诸多的不合理中找到可以合理的解释,他给他的痛苦找到了一个支点,为他的绝望撬动了一个缝隙。伯格曼不会喜欢人们这么喜欢他的电影,人类社会的消费时代到来,很多人移居到幻想里,伯格曼作品的被供奉,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当电影被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当做一种公共的调情手段时,伯格曼作品里弥漫的痛苦,就有了长矛与风车的荒诞和绝望。2022 年 7 月,我们纪念伯格曼去世,也是祭奠一种电影语法、一种美学精神,一种哲学般的影像思考方式就此断裂。人类电影史拐了一个弯,进入到另一个甬道里。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3.0成为伯格曼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里,囚徒们看见被映在墙壁的影子,误把那当做一整个世界。几千年后,一个叫伯格曼的孩子被关在家里的壁橱里,作为体罚。这里不是野蛮而荒凉的洞穴,但对一个孩子来说,漆黑一片,暗处不知道会有什么精怪鬼祟,伯格曼爱胡思乱想,就更加觉得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可怕的东西,这惩罚对他来说糟糕至极。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壁橱了藏了一支能发出红绿光的手电筒,每次被关在里面,就打开它,照出光亮,照出自己的影子,想象那是一部电影。说不定千年前的囚徒们并没有错,一点光,一点阴影,就是一个世界 —— 电影的世界。伯格曼从小,就领略过光与阴影的魔法,遁入其中。那个电影世界里的伯格曼逐渐有了雏形,有了 “胚子”。带他领略电影魅力的,是他的外祖母。外祖母算是个影迷,时常去看电影,而只要这部片是老少咸宜的类型,她总会捎上伯格曼。小伯格曼对电影的兴趣,就这样建立起来。不止如此,在外祖母家的日子里,伯格曼养成了沉思的习惯。他喜欢躲在角落里,用模型玩具布置小剧场;或者是静静望着天花板,观察光影的变化。也许这就是伯格曼对于布景、用光、调度最初的思考。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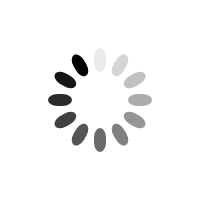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看电影(2022年第7期)
本期主要内容《野蛮生长》《大神中的大神》《婚姻的衍生品》《注视伯格曼电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