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4.0渣与不渣,都需要勇气
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渥伦斯基,按照现在的口吻就是渣男,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用这么低能的一个词去涵盖,这太简单了。当然这可能因为是在网络上,用这么一个词就可以简单地来定义。但是分析文学作品,或者从事影视这一块,如果也用这个标准的话,真的是太幼稚了。 按照 “三观不正”,那《锁琳琅》一文中一直单身、然而桃花不断的阿强,是否归入 “渣男” 一类呢?如果考虑到实际,或者复杂的人性,金宇澄笔下的阿强 ——《繁花》里小毛和阿宝的原型,蛮有意思。不信,你可以看看文章。这块地方是本人的青春化境,是自身年华飞度的客厅,这里曾经出入过多少 1970—1980 年代弄堂美女、菜场风流少妇、女店员、独身女子、时髦老阿姨、“老妖怪”、出格女生(时称 “赖三”),种种笑貌鬓影,阿强烂熟于胸 — 从哪一年哪一天起,店里逐渐就消失绝灭爽身粉、钻石牌发蜡的气味了?多亲切的女人的味道。生意逐渐逐渐清淡,店里的猫也老了,当年几个察颜辨色、油嘴滑舌的师傅也已经木讷迟缓,闲来不再拈了兰花指,对镜细梳日益稀疏的白发,天晓得,他们曾经都留有那种锃光油亮、“梁波罗” 式的分头。再以后的以后,老派铸铁白珐琅理发椅子,老式钢丝烫头罩,本白补丁布围兜,“胜家” 白铜电吹风,秃毛白鬃肥皂刷,美式趟刀布,老牌德国剃刀,“三友” 花露水及其他的名堂,都于某一时某一刻忽然消失了。这个玉石俱焚的年月,正也是阿强供职的国营工厂关门大吉之时。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5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读者见面会,又见金宇澄。金老还是讲《繁花》比较多,对新书仅做了一点铺垫介绍,极具上海爷叔的做派:从不吃相难看,笃悠悠。 新书还没到,回家找出《洗牌年代》重读,“洗牌” 里的很多人和事,在 “繁花” 中都有涉及,但 “洗牌” 的内容更杂。一段段流淌的文字在脑中勾勒出一幅幅画面,感受一座城市兜底翻时的惊讶与惶恐,在一堆堆男男女女的情事中,体会金老对人尴尬处境的深深怜悯。无论是发情的马,还是丢掉沉重年糕的女知青,抑或面对母亲陪嫁棉被恸哭的青年,都令人心情沉重。将钻石耳环塞入鸡蛋的大伯母,让我想起了蓓蒂的结局,她就像那只现实猫,不知道落入谁人之口。雨夜里装满金条的饼干罐,废品堆里的名家字画、古玩,沙发里藏着的珠宝、股票,时刻提醒我任何时代都是洗牌年代,财物、地位在不同人之间流转,即便当下也是如此。 哎,真不该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夜晚看这种书。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3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读一位 “有鬼论者” 小说稿,全文细写某人在中心医院,白日撞鬼的经过 —— 作者与鬼怪总有牵扯,屡遭麻烦,小说结尾,讲他经过省中心医院走廊,很晦气碰到一接尸车,他立刻躲入附近电梯,多次按钮,梯门纹丝不动,他明白有鬼挡门,惶恐犹豫之间,电梯的超重铃声忽然嘟嘟嘟叫个不停,让他意识到,鬼怪已聚集电梯,他已被鬼所围,于是大骇,夺门狂奔出去…… 愉快轻松的叙事,只有《何典》的江南鬼话,讲了鬼家、鬼兄弟、鬼男女、鬼情事,名称繁多,活鬼、活死人、饿杀鬼、牵钻鬼、臭鬼、扛丧鬼、雌鬼、形容鬼、六事鬼、色鬼、轻脚鬼、豆腐羹饭鬼、谗谤鬼…… 这精神与名称被鲁迅称道。人生最重大的变化,应该不是鬼,古人说死比天大,当然在日常流行剧或网络语言里,也随便出现 “去死吧!” 对白。上海的普通家常女人,完全不是一般附会的三十年代月份牌、四十年代摩登旗袍形象,满脸满身有人间的烟火,她们常用 “死人”“死腔” 口头禅,凭其声气的强弱软硬,判断她们是表示愉快,还是愤怒。沪语 “屈死” 一词,也是上海妇人的常用语,在开心、发嗲、扭捏、亲密时刻,更可前置一个 “阿” 字 —— 称呼对方(大多为男子)“阿屈死”,更能表达一种柔情与怜爱,这与北方 “打是亲骂是爱”,北方女子说的 “死鬼” 相似,爱恨交织,随意顺口。只是沪语版这三项的语气,忽然转换,即也就是 “吵相骂” 最有力武器。50 后、60 后上海女子,在公共场合厉声相骂对方 “死人”“死腔”“屈死”,后一句的态度,更有某种的不屑 —— 巴望对方的速死,必是委屈中的死,极不安的死,“死有余辜” 的死 —— 沪语 “口眼不闭”,即 “死不瞑目”,“死”,理该夹带更多遗憾才好。最接地气也最丧气的,是沪剧的通俗经典,童养媳角色阿必大,一可怜的旧上海小女子,永是在公开场合,面对广大沪剧观众,被其恶婆婆无穷无尽当台辱骂,婆婆一口浦东本地话,屡斥她 “死人!”“死货色!”“死不临盆!”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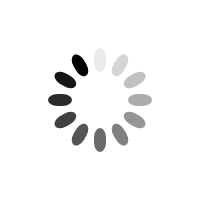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洗牌年代
上海是一块海绵,吸收干净,像所有回忆,并未发生过一样。 《洗牌年代》是作家金宇澄散文经典,二十八篇散文构筑出繁花似锦的景观意象:往来变幻的人与场景,老上海原腔原调的市井日常,东北农场的冷冽传奇,手工器物的工笔描摹……摊开来看,是一幅上海的老画卷,一个特殊年代的清明上河图;收拢来看,是永恒的人心人性与精神欲望。《洗牌年代》是《繁花》的素材本,上海的老故事集,《繁花》中诸多人物、故事均脱胎于此;亦是一卷沪上物质生活史,详实还原上海人曾经的生活方式,叠化出往日的原貌。在画面、色彩、气味和声响之下,故事暗流涌动,自由、华丽、动人的细节,如水银泻地。 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洗牌年代》抓紧了物、人、空间、气味,它们兜合出故事的细流,复活上海的地理空间与城市积淀。人物在其间行走,生命的种种兴味、内在的热情、被按下不表的故事,投注于具体物件之上,是世俗生活的微缩,显现出恒常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