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4.0制造一场大屠杀总共分几步?
总共分四步:第一步,中介化。先在人与人之间插入一个中介,这中介可能是一张表格、一张钞票或是一部手机,于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中介实现间接联系。就像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在人与物之间插入一个价格,物体相对于人的 “赤裸裸” 的使用价值,变成了 “遮遮掩掩” 的交换价值,这也是人的异化的第一步。第二步,零件化。福特发明的汽车流水线大家都知道,其实原理一样,就是把一件事情拆分成无数个细小的步骤,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只需要重复做好自己手上的那一份简单工作,无需对全局负责也根本看不到全局。因此,一个办事员的眼里不再有活生生的人,而只有一堆应付绩效考核的数字。第三步,去目标化。人已经变成螺丝钉,螺丝钉能有什么大目标?螺丝钉只是一颗螺丝钉,看不见全局,更看不见组织的终极目标,它只要老老实实地呆在工位上,扮演好分配给自己的角色即可,至于组织这艘船要开到哪里去,它不想知道也无从知道。第四步,非人化。走完前面三步,“人” 就基本上消失了,主体变成螺丝钉,对象变成考核数据,人的异化也就完成了。以上都是现代性带来的结果,是追求理性和科学的副产品。谁能想得到呢?但它就是出现了。你觉得大屠杀已经过去了?不,它还在。你觉得大屠杀离我们很远?不,它很近。现代性如此强势,把绝大多数人都裹挟进来,用韦伯的话来讲就是 “现代的牢笼”。每一个身处体制之中的人都应警醒,你大概率逃不掉,但时不时也要从工位上站起来,往前方望一望,当初那个目标还在吗?辛德勒就是一个从工位上起身的人。马克思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是有必要的。另外,这本书之所以扣一颗星,是因为长句太多、段落太长,理论虽然不艰深,但读起来实在费头发。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担忧并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职业上的原因 ——— 尽管它对于社会学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学的社会关切度有极大的损害。使这种状况更加让人坐立不安的是我们知道,如果 “大屠杀能在其他地方大规模发生,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它包含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之中,而不管你喜欢与否,奥斯维辛像人类登上月球一样扩展了全人类的意识领域”[19]。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以平静的;比如 L. 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 而联合国从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20] 大屠杀浩劫事后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在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各种社会原则那些本身尚未引起注意的 “其他方面” 的可能。这样说来,我认为已经被历史学家全面研究过的大屠杀的历史应当被看做一个社会学的 “实验室”。而在 “非实验室” 的条件下无法被揭示并因此在经验上无法去接近的社会特征已经被大屠杀揭示和验证。换句话说,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现代性的弊端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求所养育的。马克思韦伯认为官僚制度是处理大量文书工作的最有效手段;其次官僚制度强调可计算性 / 量化性,这有助于人们对成功做出估计;第三,制度性的法规让官僚体制以高度可预测的方式运作;第四,官僚制度通过非人的技术来代替人力实现管理。官僚体制中的成员就像机器一样在体制中高速运作着,排除个人思想,极少带有自己的判断。因此官僚制度对于一个组织是高效的,零件是可替换的,却是对个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需要,然而在官僚制度下,绝大多数人都厌恶劳动,在劳动中觉得自己不是自己,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己。而且官僚制度弱化了个人的责任感,抹杀了个人行为的道德意义,也就促成了大屠杀的发生。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现代性的道德世界与其说是由善与恶勾勒出来的,不如说是缘于人们「不能处理权变性和矛盾性」的无能。鲍曼在书中反驳了这样的观点,即大屠杀可以被理解为对原始野蛮的一种反常的回归,这种野蛮根源于前现代传统的偏见,是一种与向现代化文明前进的长征的特殊偏离。相反,他认为,大屠杀所呈现的杀戮的工业形式和大规模特征,实际上正是由于现代性才变得可能。现代性为大屠杀提供了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一方面,现代主义的社会工程意识形态,相信社会可以按照某个人的理想愿景来塑造。鲍曼用手术和园艺的比喻来强调这种意识形态对那些不适应这种愿景的、不那么强大的群体的意涵和影响。他们变成了需要切除的病痛部位,要被根除的杂草,以追求健康的身体,修剪整齐的草坪。在这方面,纳粹类型的激进反犹太主义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一个庞大和有效的官僚机构的存在,以及强大、集权化的国家政策体系的存在,提供了将意识形态愿景变为现实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因为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而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这种社会压制又来源于在意识形态上被污名化的受害者,与强调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的理性的官僚和国家官员之间被创造出一种社会的和道德的距离。鲍曼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曾经存在于现代性之中:"是各种因素的‘结合’,而不是那些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才是不寻常和罕见的"。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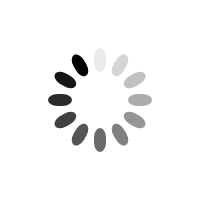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现代性与大屠杀(人文与社会译丛)
本书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