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3.0这个世界是那么的不平衡,哪怕是电影
这个世界上,说话有人听的国家其实不多,这是政治,干活有人管的国家也不多,这是经济,折腾有人看的国家更不多,这是文化,出事有人怨的国家还是不多,这是社会。即使是在电影的世界,依然还是这样,除了五常国家,其他国家的电影竟然都是小众。就算是日本,印度,巴西这样的二流强国,大家耳熟能详的仅仅是寥寥,而整个非洲,东南亚,西亚,拉美,真是拾遗补缺,不禁令人唏嘘在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顺着这一角度眺望过去,置身于当代电影的生存游戏里,诗意已经是一种危险品了。大家都默契地认定它是不可捉摸、不可限定与不可追索的,小心翼翼地摘除它和电影本就微弱的关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掩盖诗已经无用的事实。大家就仍然可以在一部从一开始就摒除了诗意的电影上映后,继续大言不惭地谈论诗歌和浪漫。毕竟诗歌和浪漫仍然对一小部分人有效,这部分人仍然愿意为一些不可捉摸和不可追索的东西去买单。也就是说,在电影的语言体系里,从来就不缺少美、浪漫、爱这些和诗歌有关的气息,只不过它曾经是电影的母语,现在被绝大部分人当成了电影的装饰品。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6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我们生存的原因在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顺着这一角度眺望过去,置身于当代电影的生存游戏里,诗意已经是一种危险品了。大家都默契地认定它是不可捉摸、不可限定与不可追索的,小心翼翼地摘除它和电影本就微弱的关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掩盖诗已经无用的事实。大家就仍然可以在一部从一开始就摒除了诗意的电影上映后,继续大言不惭地谈论诗歌和浪漫。毕竟诗歌和浪漫仍然对一小部分人有效,这部分人仍然愿意为一些不可捉摸和不可追索的东西去买单。也就是说,在电影的语言体系里,从来就不缺少美、浪漫、爱这些和诗歌有关的气息,只不过它曾经是电影的母语,现在被绝大部分人当成了电影的装饰品。李沧东在拍摄 [诗] 的时候,已经知道诗正在现实里死去,他希望可以在电影里给诗歌一个继续存活的机会,哪怕是在两个绝望的人中间,哪怕其中一个人已经患上了健忘症。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导演,李沧东希望 “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电影,又是现实。或者觉得这好像是现实,又是电影”。似乎和诗歌一样,像李沧东这样的电影人也已经在电影的现实里凋零了。我们知道在电影的历史里,有些电影人也是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电影,同时是写给人类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他们讲述爱、浪漫、美,也吟唱痛苦、孤独和黄钟大吕一样的悲怆。比如 [野草莓] 里梦境和现实的解脱与迷失,宛如一场生命的探戈。比如 [雾中风景] 里女孩坐在卡车边上,血顺着大腿流下,有人在雾中呼唤,但她神情冷漠,恍如一个旁观者。比如 [青木瓜之味] 里,小女孩梅在南洋的骑楼下如木瓜一样长大,每一个枝丫里都满是热带水果的香甜和佛堂的烟尘。在西贡修剪得工整的植物中间,她是不动声色的欲望。比如 [中央车站] 喧哗的人声之外,有一个女人为远方的人书写。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好像都曾有过这样的车站,你从这里出发,去抚慰破碎的四月,然后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又回到了这里。发现四月将尽,人生已无重来的可能。这些电影不是诗歌,而是一种记录,我们把它们当做诗歌,是因为它们如诗歌一样勇敢。在一个趋于统一的语境下敢于记录那些小众的、独特的、落伍的、日常的事物,敢于用一种不流行、不迎合、不轻巧甚至是未知的方式,体验人生。这些影片的导演也不是诗人,他们更像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一个思想者,或者说是一群不快乐的人,比如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他在寻常的事物里发现了那些可能到来的危机、可能消散的美和可能转瞬即逝的幸福。就像诗歌的背后是伤痕,他们以拍摄的方式游吟在古老的大地上,他们是那些最终站到了桌面上的人,他们牺牲现实生活里平庸的快乐,点燃了人类高贵的痛苦。在 [死亡诗社] 的结尾,约翰・基汀被迫离开,学生们站上书桌,朗诵诗人惠特曼为悼念林肯而写下的名篇《船长,我的船长》,那首诗的最后几行里有以下字句,“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时间说的是现在,但最终说的还是恒常。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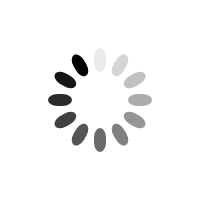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看电影(2021年第11期)
本期特别报道《网球巨星培养指南 国王理查德》《回归传统 魔法满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