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早期汉学经典之作 | 孙健教授推荐
从 17 世纪开始,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往来变得频繁和密切。随着西方探险家到达广东沿海,基督教传教士也很快来到中国,其中起引领作用的是耶稣会。
为了确保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顺利进行,耶稣会士逐渐摸索出一条 “适应政策”,使基督教文明迁就、适应中国文化传统,甚至试图通过基督教与儒学的结合,来促成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 。
同时,耶稣会士收集举凡有关中国语言、历史、地理、政治、哲学、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以书信、报道、著作等形式传回欧洲,引发了欧洲学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问题的热烈讨论,涌现出很多早期汉学经典之作,格鲁贤的《中国通典》就是其中之一。
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密不可分,身处欧洲的人们想要了解中国,必须依赖于耶稣会士传回的资料。法国重农学派的创立者魁奈在撰写《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时,就曾述及研究资料的难得,提到除了传教士的报告以外,几乎没有可资依据的东西 。
格鲁贤一生从未踏足中国,他的著作同样建立在来华耶稣会士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冯秉正于 1703 年抵达澳门,在中国生活了长达 40 余年,他的《中国通史》是据满文本《资治通鉴纲目》编译而成。康熙皇帝为使满语传世久远,下令将《资治通鉴纲目》译成满文,继而又命冯秉正转译为法文。翻译工作持续了六年多时间,1737 年,译稿被寄回法国。
杰出学者、巴黎金石与美文学院首位常任秘书弗雷烈对译稿极为重视,希望担任该书的出版人,由法国国王出资在卢浮宫印刷。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一部值得由皇家印刷部印制的杰作。这部中国信史在法国的出版,同样应该充满权威性,就像它在中国由康熙皇帝命令下出版那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通史》迟迟未能出版,冯秉正的书稿被尘封在里昂图书馆中。负责管理该学院的地方行政官注意到冯秉正的手稿,由于这些手稿写在中国纸张上,在运输和保管者手中辗转时有部分受损,里昂大主教为将手稿保存下去,决定将它重新粘在画布上,这保证了手稿的完整性 。1775 年,图书馆将手稿向格鲁贤开放,以促成其出版。汉学家、“国王读书顾问、王家学院阿拉伯文教授、国王陛下东方语言翻译”,戴索特雷帮助修饰了冯秉正的译文。
1777 至 1783 年,格鲁贤陆续出版了十二卷本的《中国通史》。他事先于 1776 年 3 月在《文学报》刊登书讯,吸引了很多读者预订,订金达到 86000 法郎,为出版提供了资金。 书籍售价 90 法郎一套,虽然价格不菲,仍不乏追捧者。书中登载了 530 位订购者的名单,随着订购者的增加,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又被登载于不同的卷册中。在最后一卷出版两年后的 1785 年,格鲁贤又增加了由他自己撰写的第十三卷,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中国通典》。第十三卷出版后大获好评,甚至单独售卖,三个月后就出版了第二版,又被译为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在研究范式和结构框架上,《中国通典》代表了 17、18 世纪欧洲很多汉学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即不局限于某一个固定领域,而是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广泛包罗在内,对整个中国或其文化进行考察。《中国通典》的前半部分谈论中国的自然条件,包括中国各省份、鞑靼地区、周边国家的地理面貌,城市、人口、交通、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和中医药材等;下半部分讲述中国的文物制度,包括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队纪律、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因此,这本书是又一本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力图对中国展开全景式描述。
在内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通典》对欧洲 “中国礼仪之争” 的回应。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 “适应政策”,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引起其它修会的反对,在欧洲酿成沸沸扬扬的 “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发生耶稣会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之间,同时吸引很多欧洲学者参与其中,从 17 世纪初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中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三个问题:“天主” 的译名,尊孔和祭祖的礼仪。
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是发端于诺亚的东方文明,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中提到的 “天” 和 “上帝”,就是基督教的造物主 “天主”,因此中国存在原始的基督教信仰。郭弼恩称:“中国的哲人和最初诸位皇帝所宣扬的宗教与基督教是同一宗教,他们敬仰基督徒所敬仰的同一上帝,与基督教徒一样承认上帝是天地的主宰。” 这种看法引起其它修会的广泛批评,在他们的推动下,教廷下令禁止使用 “天” 和 “上帝” 来指代基督教的 “天主”。
格鲁贤在《中国通典》中对中国宗教的论述,秉承了耶稣会士一贯以来的看法,他在述及中国的宗教信仰时,开宗明义就引用了钱德明的论述:中国人的原始信仰甚至要早于摩西受神的指令而在《圣经》中所做的解释之前;这个民族的传统认知,可以上溯至四千年前的诺亚。
随后,格鲁贤论述到:所有的历史痕迹都显示,诺亚的直系子孙在中国繁衍。越上溯历史根源,真正的信仰痕迹就越显著。这些原始宗教的痕迹也记录在最古老的民族典籍中,中国经典中无处不在宣示着上帝的存在,它被称为天、上天、上帝、皇上帝等,这些名字与我们使用的 Dieu、le Seigneur 等是一样的。
因此,古代中国人所尊崇的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智慧的、自由的、全能的上帝。中国古代皇帝的这个宗教教理一直在随后的朝代中得到延续,所有好的君王,他们的继承人,都对上帝心怀敬畏。这个关于神的存在和其象征的看法,关于神的教派和崇信在中国由来已久,多个世纪以来没有遭到破坏和混淆。
无论在研究范式、结构框架,还是在具体观点方面,格鲁贤相对于前人而言都未能有太多创见,《中国通典》更多只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而不是开拓和创新。在今天看来,格鲁贤的很多论述显然是荒谬的,但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从知识的角度出发,用今天的知识结构去评判二百多年以前研究的是与非,恐怕并没有太大意义。相比之下,尽量尝试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深入到知识形成的具体过程中,探寻并揭示可能影响知识形成的动机、细节和因素,把握知识形成的脉络,可能更为重要。
格鲁贤的《中国通典》是依附于冯秉正的《中国通史》而存在的,他在《中国通史》前言中写道:《中国通史》是 “唯一一部可以解决我们的疑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君主帝国历史的著作” ,“今后欧洲文化阶层在涉及到古代、现代中华帝国的政权、制度、进步、战争和变革时,可以从这部原始文献中引用可靠、精确、详细的知识。” 这段话既是格鲁贤对冯秉正《中国通史》的评价,也未尝不是他对自己撰写的《中国通典》的期望。作为《中国通史》中的一卷,《中国通典》的用意即在于证实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宗教的论述是真实无误的,从而为耶稣会士提供支持。
然而时代的发展使格鲁贤的良苦用心付诸东流。《中国通史》出版的 18 世纪 70、80 年代,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与 40 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礼仪之争” 的发展给耶稣会带来灭顶之灾,1764 年耶稣会被宣布废除,1773 年被教廷解散。
自 17 世纪以来,耶稣会就是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最主要传播者,同时也是汉学研究最主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它的解散使欧洲的汉学研究遭遇挫折。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 “中国热” 在 18 世纪中后期降温,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如魁奈、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相继于 18 世纪 70、80 年代去世,法国思想界进入一个相对的低潮期,这使《中国通史》未能在思想界激起足够的回应。
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扫荡了一切,汉学研究也在劫难逃,一直到 1814 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开设以后,法国才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汉学研究,但其研究范式已经与此前的传教士汉学有了根本区别。冯秉正《中国通史》,乃至格鲁贤《中国通典》的出版,正处于一个时代变换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是正在走向终点的传教士汉学的一部绝响。
由张放、张丹彤两位学者翻译的这部著作,无论在内容的忠实性还是语言的流畅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译者秉持严谨的态度,对原著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以脚注的形式加以注释说明,从而减轻了读者在阅读此书时的困难。
当然,由于格鲁贤所处的时代还未建立起完善的学术规范,也给全书的翻译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在谈到佛教的时候,格鲁贤写道:“一个如此奇怪的哲理,你不相信它能在中国找到信奉者吗?然而高宗皇帝如此执迷于此,竟然退位去追随这个荒诞的教义。” 由于格鲁贤未注明出处,致使译者也未能确认文中 “高宗皇帝” 的确切身份。事实上,文中提到的高宗皇帝是指宋高宗,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提到,宋高宗因信奉佛教而将皇位禅让给宋孝宗 ,格鲁贤在此处援引了杜赫德的说法。类似这些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当然这无碍于译本在整体上的优良。
(作者孙健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1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4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代表了由“传教士汉学”到真正意义上汉学的过渡 | 张西平教授推荐在汉学发展历程中,早期汉学是由传教士开辟的,虽然那时还没有 “汉学”(Sinology 或 sinologie)这一称呼,但专业汉学出现(以法兰西学院 1814 年正式设立 “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 为标志)之前,传教士已经作了 200 多年的研究工作。
这 20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主要的也是最早的开拓者是耶稣会士,随后有方济各会等修会参与其中。这些研究成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前身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推动下,大象出版社仅仅在 2000 年以后,就出版了 50 余种,功不可没。我自己作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对这一过程十分熟悉,这些著作中绝大多数也是我推荐和促成出版的。
关于张放与张丹彤合作翻译的这部书《中国通典》,是法国耶稣会汉学家格鲁贤的代表作,该书是是继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之后,又一部对中国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而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
译者在《翻译序言》中,对这部书的介绍,写得十分中肯,学术性很强,我只想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推荐:
第一,这部书,是传教士汉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具有通史性,学术价值非常高。和大象出版社以前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图说》等译著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第二,该书译者是一位老学者和一位后起之秀。老学者张放教授对法国汉学有多年研究,他曾翻译出版《(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 —— 远西对话》。年轻学者张丹彤于 1999 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Université Pierre Mendès France)获得双硕士学位,译著颇丰,目前也正在翻译早期传教士的著作。因此,这部书的翻译质量是十分可靠的。
第三,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梳理西方汉学的历史,摸清其发展学术脉络,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作。这部学术著作,是专业翻译人员和有汉学出版丰富经验的大象出版社相结合,它的出版将弥补我国西方汉学名著翻译的一个空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通典》作为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著作,可读性和研究价值都很高。
(作者张西平教授,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方汉学史方向)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代表了由“传教士汉学”到真正意义上汉学的过渡 | 任大媛教授推荐书评法国耶稣会士格鲁贤的著作《中国通典》,已经在海外冰藏了 200 多年,而中国学术界尚不能以中文的形式阅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早已经开始从学术的角度展开深入的研究,这不仅是 “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需要,也是 “文明互鉴” 的需要;另外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也相当注意这部著作,这一点,从西方近年的出版目录检索,就可以清楚看到。
我本人看到这部书,是通过英国的 Lust 目录的微缩胶片,是 1787 年版本(Grosier; J.B.GA.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787. 2 vols. [JL.30] 15 microfiche Order no. LHT-521/1)。而翻译者使用了更早一点的版本,其学术价值可能更高。西方近年的重印本很多,也有英文译本,这说明了这部书在西方被重视的程度。如果我们再不能使中国学术界和读者见到中文译本,在开展同西方学者关于 “汉学” 的对话中,就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毕竟多数中国读者(也包括学术界)能够直接使用西文的比例还不是太高。
我在以上使用 “汉学” 这一概念,对于这部书来说,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传教士或者是利用传教士的文献资料形成的学术著作,还只能是汉学的先驱。但是,这一前期工作,持续了有 200 多年的时间,其成果,十分重要。就这本书而言,特殊的意义在于,这部著作,可以说代表了由 “传教士汉学” 到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的过渡。因此,这一著作,也是 “传教士汉学” 的前驱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或者说佼佼者。
关于这部书在内容上的价值,译者的《翻译序言》中已经有客观公正的介绍,不必赘言。但我想应该补充的是,从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的角度,这部书也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它出版于 230 多年前。书中对中国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草药材等等的描述,关于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军队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等的叙述,在今天看来,也是重要的史料。
我还认为,大象出版社,积 20 多年海外汉学著作翻译出版的经验,出版这部著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坚持学术本位立场,就是要出这类著作。故郑重予以推荐。
(作者任大媛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史教授)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赞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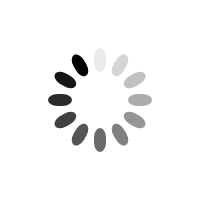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中国通典(全二册)
《中国通典》是作者格鲁贤,通过与来华耶稣会士、相关科学院、图书馆的密切联系,获得了大量的中国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高屋建瓴、纵横排阖的利用,以及有效的文献考证,使得《中国通典》这部集中国知识之大成之作问世。 可以说,《中国通典》是继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之后又一部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对中国进行介绍的汉学书籍,在西方汉学领域堪称经典,对当时的法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通典》不啻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库。 中国本来就是一本大书,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万花筒式地观察和描述,我们不仅可以获得文史哲诸方面的基本知识,也能得到300年前中国五花八门的趣闻和信息。 全书分上、下两册,1787年法国国王特许新版,你所看到的是该书的首个中译本。 上册讲述构成中华帝国的十五省、鞑靼地区、岛屿、从属国的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地方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医药草药材等;下册涉及清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纪、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对于了解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被认知程度、中西文明的交流程度,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清王朝闭关锁国? 在中国,康熙皇帝自幼钦佩传教士们的科学素养,他于1693年7月决定委派白晋神甫为特使,返回欧洲去招募更多的有学之士来华相助。 欧洲引领时尚潮流? 1700年1月7日,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穿着中国式服装,坐着八抬大轿,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舞会上,令举国上下震撼不已,这助推了欧洲的“中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