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盒子上的精神窗口
每日一书:《伟大的电影》。全美第一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撰写的 100 部伟大电影的评论。这 100 部 “伟大的电影” 几乎都是看不到的老片子,即使在电影文化极度繁荣的美国,这些影片也正在被人遗忘;而在中国,这些影片就更加不为人知。我们生活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盒子里,电影则是盒子上的窗口。电影允许我们进入他人的精神世界 —— 这不仅意味着融入银幕上的角色(尽管这也很重要),也意味着用另一个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电影看多了,不知不觉就会把导演们当成老朋友,对他们的好恶了如指掌:布努埃尔对人性的厚颜无耻最感兴趣,斯科塞斯关注宗教罪恶感的无底深渊,黑泽明歌颂身处于充满敌意的大环境下的个体,怀尔德往往震惊于人们为了追求快乐而做出的举动,基顿表现的是人的意志如何挑战物理条件的限制,而希区柯克创造的影像犹如罪人的梦魇。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2001:太空漫游》的天才之处不在于其丰富,而在于其简洁:没有一个镜头是仅仅为了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拍摄的,只有对自己的才华怀有无限信心的艺术家才敢于创作这样精炼的作品。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梦魇,它讲述了西班牙征服者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1502—1548)在传说的诱惑下于 1560 年至 1561 年间率领一队人马深入秘鲁热带雨林寻找失落的黄金国,最终几乎全军覆没的故事。有些人节假日期间有地方可去,有些人却无家可归,这两种人之间横亘着一道悲哀的鸿沟。《公寓春光》这部影片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一反差的存在。我们的一切生活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栖息在大自然饥饿的血盆大口之上,一不小心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吞下去。幸福的生活在这种脆弱面前只是日复一日的缓刑。如果一定要在查尔斯・卓别林的作品中选取一部,那么《城市之光》或许最能体现他全方位的才华。这部影片包含了滑稽剧(slapstick)、情节剧、悲剧、哑剧,有轻松自如的肢体动作,有粗俗大胆的噱头,也有精致优雅的细节,当然,还有那小流浪汉 —— 这个角色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影片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核威慑系统即使能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我们也很难说它究竟 “威慑” 了什么。这一论点毫不客气地戳穿了冷战的本质。每个热爱电影的人早晚都会遇上小津。他是所有导演里最安静,最温柔,最具有人文关怀,也最平和的一位。但他的电影里流动的情感既深刻又强烈,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家长和孩子,婚姻或独身,疾病和死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怀。杰克对女人怀有一种矛盾的情绪,这种情绪被弗洛伊德命名为 “圣母 - 娼妓情结”(Madonna-whore complex)。在拉莫塔眼中,女人失身之前都是不可接近的理想处女,但(与他)发生关系之后就遭到了玷污,从此便成了怀疑的对象。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真是一件自然与艺术的杰作。她并没有老化成一个标志,或某个属于过去的公民。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她也依然不断创造着自己。梦露有种天赋,使自己的对白看似得自偶然而幸运的灵感。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740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5.0我们生活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盒子里,电影则是盒子上的窗口。这本书让我去一个个打开那些不属于我们的年代的神奇盒子。《2001:太空漫游》(斯坦利・库布里克 1968):没有一个镜头是仅仅为了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拍摄的,每一个场景驻留在银幕上的时间都足以令我们充分思考,并被永远纳入我们的想象之中。科幻 + 古典乐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只有少数电影能达到崇高的境界,像音乐、祷文或壮丽的风景一样震撼我们的头脑、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令我们茫然自失。大多数电影仅仅讲述片中人物如何克服惊天动地或滑稽可笑的困难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而《2001:太空漫游》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探索,一种需求。它既不用特定的情节转折点来引人注目,也不求我们与角色产生共鸣。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会思考时,我们才成了真正的人。我们的头脑赋予我们工具,让我们有能力理解自身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我们应当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并非生活在一颗孤独的星球上,而是居住在群星之间,我们并非无知肉块,而是智慧的生物。《恐惧吞噬灵魂》(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1974):他们和我们对立。去掉所有的跌宕起伏,只留下平稳而安静的绝望。他们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互相喜欢,互相关心。《现代启示录》(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9):一个名叫柯兹的欧洲人进入刚果丛林的最深处,在那儿把自己变成一个上帝般的领袖。一艘小船出发去寻找他,在整个过程中,故事的讲述者逐渐对条理井然的现代文明失去了信心,周围的丛林就像一个残酷无情的达尔文主义试验田,其中的每个生物每天都尽量不成为别人的美餐。在旅程的终点所找到的并非柯兹,而是柯兹所发现的东西:我们的一切生活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栖息在大自然饥饿的血盆大口之上,一不小心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吞下去。幸福的生活在这种脆弱面前只是日复一日的缓刑。《卡萨布兰卡》(迈克尔・柯蒂兹 1942):既然不知道风向哪边吹,她也就无法偏向于任何一方。它从来都不会因为过分的熟悉而失去光彩。就像一张最中意的音乐专辑,听得越多,喜爱越深。黑白摄影不像彩色摄影那样会随着时间变老,对白既节约又愤世嫉俗,情绪效果也大多是在不经意间达成的。《公民凯恩》(奥逊・威尔斯 1941):“玫瑰花蕾” 就是盖茨比夜夜守望的码头尽处的绿色灯光;就是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追寻什么;就是《2001:太空漫游》里猿人抛向空中的那块骨头。它代表着对生命中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的渴求,而大多数人长大之后就会懂得克制这种非分之想。“玫瑰花蕾” 这个词什么也说明不了,但它恰恰证明了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说明白的。《城市之光》(查尔斯・卓别林 1931):小流浪汉更像一个哑剧演员,总是独立于其他人物的人生与现实之外,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他无家可归,孑然一身,世人眼里只有他的外表,而他只有通过身体动作才能与世界沟通。尽管他有时也做出说话的样子,但他其实根本不必开口。小流浪汉即使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也可以毫无障碍地生活。默片中没有对话,没有生硬的超现实主义,其节奏流畅自然、不受干扰,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底。孩子们长大之后便忘记了如何倾听无声的语言,然而那些电影却仍然耐心地等待着,时刻准备把这种智慧再一次传给他们。《绕道》(埃德加・G. 乌尔莫 1945):犯罪电影和黑色电影的区别在于,犯罪电影中的坏蛋知道自己很坏,而且希望如此,而黑色电影的主角认为自己是好人,只是被生活给涮了。《奇爱博士》(斯坦利・库布里克 1964):核威慑系统即使能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我们也很难说它究竟 “威慑” 了什么。人类设计的机械按照完美的逻辑运行,但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想搞笑的人永远不如想严肃却严肃不了的人搞笑。《毁灭天使》(路易斯・布努埃尔 1962):布努埃尔尖刻地指出我们都暗藏着野蛮的本能和不可告人的秘密:把一群富有的晚宴客人关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会互相攻击,像人口过剩实验里的老鼠。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这部电影最好的解释就是它没有解释。《浮草》(小津安二郎 1959):就像一段熟悉的音乐,让人可以从中寻找安慰。它是如此的注重氛围 —— 把观众深切地带入那个炎炎夏日里安静的小渔村。里面的角色就像邻居一样。电影的故事并不悲伤,中心角色是一个性格健全的演员,他试图依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生活,结果惊讶地发现其他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意志。他的摄影机从不运动,总是比角色低一些,以违反视觉构图的传统规则而闻名,有种沉思冥想的气质,鼓励我们去仔细观看并让自己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教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2):故事从头到尾发生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能使我们完全站在黑手党自身的角度来看待黑手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竟会对那些实际上十恶不赦的人物产生同情。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秘密,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取代了现实世界,在这个社会中,教父执掌大权、主持正义,唯一的恶人是叛徒。这个社会只有一条戒律,那就是迈克尔所说的:“永远不要和家族对着干。”《乱世佳人》(维克多・弗莱明 1939):对时光的流逝表达了真实可信的情感,尽管这种文明已经逝去,但并没有被人遗忘。“有一片骑士的土地,遍地棉花,人们称之为老南方。这个贵族的世界,折射出骑士时代最后的光彩。这里有最后的骑士和他们的佳丽,最后的奴隶主和奴隶。这一切只能在书中看到,因为他们不过是记忆中的一场梦幻,一个业已随风而逝的文明。《一夜狂欢》(理查德・莱斯特 1964)披头士和《一夜狂欢》的纯真当然没法持久。等待着他们的是作为史上最流行乐队的巨大压力,和神秘的东方之间的调情,乐队的分道扬镳,六十年代以来毒品的副作用,还有约翰・列侬的死。披头士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夏季,一个幻想破灭的秋季和一个悲剧性的冬天。但是,春天的时光是多么可爱啊。它全都包含在一部电影里。《生之欲》(黑泽明 1952):一个男人做好事的努力会启发、迷惑、激怒,或挫败那些不能身临其境的人,他们只能在外部经由自己未经省察的生活来观察。我们这些人追随了渡边最后的生命旅程,却被迫回到活人的世界,回到性恶论和闲言碎语之中。我们在心里催促着幸存者换种方式思考,去获得与我们相同的结论。这也是黑泽明实现其最终效果的方式:他不让我们成为渡边决定的见证人,而是其传道者。《奇遇》(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 1960):这些人过于浅薄,以至于连孤独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试图在与他人的接触中逃避自己对生活的厌倦,到头来却再一次找到厌倦而已。“告诉我你爱我。”“我爱你。”“再说一次。”“我不爱你。”《麦凯比与米勒夫人》(罗伯特・奥尔特曼 1971):充满对永远得不到的爱和家的渴望。不是像夫妻那样的 “和”(and)而是像公司那样的 “&”。这完全是生意上的安排,对于她来说一切皆生意。在她到达长老会教堂镇之前有过的悲痛已成过去。其他的一切也都成了过去,这点鸦片可以保证。可怜的麦凯比。他心里是有诗意的,可惜来到了一个没人知道什么是诗意的小镇上,除了一个人之外。而她却已经败给了诗意。《随心所欲》(戈达尔 1962):她在被一个顾客拥抱的时候抽着烟,空洞的眼神越过他的肩膀。后来拉乌尔吸了一口烟然后和她接吻,她吸过他嘴里的烟然后又吐出来。在巴黎,除了混酒吧、抽烟和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钱之外还有什么可做?接客对她来说并不比弹球游戏更有趣。从事皮肉生意在法国被叫做 “生活”,电影的标题由此带上另一个意义。电影没有额外的动作。它用一种冷静平稳而兴致勃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摄影机的纪律阻止了我们用情节剧的方式解释娜娜的生活。她等待,喝酒,抽烟,上街,挣钱,把自己交给遇见的第一个皮条客,放弃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有一场戏是她笑着对一个自动点唱机跳舞,我们能匆匆瞥见有一个年轻女孩在她的内部,在她的灵魂里。其余的都浮于表面。戈达尔试图用一次拍成的镜头,我们随着它的视线而看着娜娜第一次过她的生活,没有预先排演。它清晰,收敛,不动感情,唐突,然后就结束了。这是她要过的生活。《低俗小说》(昆汀・塔伦蒂诺 1994):片中的对话简洁凝练,足以与雷蒙德・钱德勒、埃尔莫・伦纳德等硬汉派名家的手笔相媲美。昆汀的幽默看似一本正经,却总使人忍俊不禁;也正如这些大师一样,昆汀在平实的叙事中揉入了粗犷的诗意与恶趣味的奇思妙想。影片的环形 - 自我指涉结构闻名遐迩。《辛德勒名单》(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993):奥斯卡・辛德勒欺骗了第三帝国,阿蒙・戈斯则代表了第三帝国的罪恶本质,他们都是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人。反犹大屠杀这个题材太庞大、太沉重,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难以承载,然而,通过讲述辛德勒与戈斯的故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找到了处理这一题材的方法。他不能给本世纪最惨痛的故事编造一个美好的结局,但他书写的结局至少证明了我们可以抵抗邪恶,甚至可以战胜邪恶。面对着纳粹的藏尸所,只有这条信念能使我们免于绝望。“这份名单就是至善,就是生命。名单的四边环绕着深深的河流。”《七武士》(黑泽明 1954):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用受虐狂式的坚韧不拔来履行复杂的社会义务。不仅仅是武士,那些强盗身上也有这种精神。他们就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那样,扮演着指派给他们的角色。《肖申克的救赎》(弗兰克・戴伦邦特 1994):影片运用旁白者冷静并洞悉一切的声音,把我们引入故事中,仿佛我们也成了这群囚犯之中的一员。与大多数影片相比,这部电影更为深刻,它探讨的是建立在友谊与希望之上,一生持之以恒的追求。一切优秀的艺术都在阐释比它所承认的更深刻的哲理。《星球大战》(乔治・卢卡斯 1977):愿原力与他们同在。跟《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公民凯恩》一样,《星球大战》也是技术上的分水岭,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电影。这几部片子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只在以下这一点上相似:它们都出现在电影史上的关键时期,新的拍摄方法已经成熟,并可以在电影中得到综合。《一个国家的诞生》把尚在发展中的镜头和剪辑的语言汇集到一处。《公民凯恩》整合了特效、先进的声音处理、新的摄影风格以及摆脱了线性模式的叙事策略。《星球大战》则集新一代特效和高能量动作片于一身,它把太空歌剧和肥皂剧连成一体,把童话故事和英雄传说融为一炉,最终打造成一场狂野的视觉之旅。《出租车司机》(马丁・斯科塞斯 1976):崔维斯的绝对的孤独让《出租车司机》成为电影史上最杰出、最有力的影片之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崔维斯・比科尔作为一个电影主人公极度缺乏亲和力,这部影片仍然让无数人产生了共鸣。对于斯科塞斯影片中的许多人物而言,救赎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这些人自轻自贱、罪孽深重,在穷街陋巷中讨生活,但他们也渴望被原谅、被崇敬。崔维斯所得到的原谅和崇敬究竟属于现实还是幻想并不重要。在整部影片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决定着他的现实,到最后,他的心灵终于给他带来了某种安宁。《一条安达鲁狗》(路易斯・布努埃尔 / 萨尔瓦多・达利 1929):路易斯・布努埃尔曾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他只能活二十年,他希望这样生活:“每天给我两小时的活动时间,剩下的二十二个小时都用来做梦 —— 前提条件是我能记得这些梦。” 这部从标题到内容都毫无意义的作品至今仍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短片之一。这部影片的创作目的是给社会带来一场革命,关于《一条安达鲁狗》的流言已经成为超现实主义者的传奇之一。“尽管超现实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但他们始终在和他们所鄙视的社会作斗争。当然,他们首要的武器不是枪,而是流言。”“任何一个有可能引起某种合理解释的想法或画面都不采用,我们必须向非理性敞开一切大门,只保留能让我们惊讶的画面,而不去寻求解释。”《人生七年》(迈克尔・艾普特):每隔七年,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就会重访一群人的生活,这项编年史工作从他们 7 岁起就开始了,现在已经拍到了 56 岁。就在艾普特与这群人聊天的时候,他的电影穿透了生命最核心的神秘:“我为什么会是我自己而不是你?为什么会在此处而非彼处?” 这些纪录片总能打动我之处是它们对电影这一媒介天才般的甚至高贵的运用。没有哪个艺术形式可以如此出色地捕捉到眼中的神采,话里的感情以及在字句间保持沉默的思想。如果你像我一样每七年都去看《成长》,你就会开始思索一项惊人的事实: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生活在时间中的动物。七岁大的小孩身上已经表现出大部分成年后的特征,无论是好还是坏。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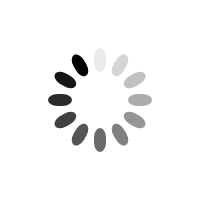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伟大的电影
在过去数年中,罗杰·伊伯特每隔一周都为一部“伟大的电影”撰写评论,给予新鲜而热忱的褒扬。《伟大的电影》一书精选了其中的100篇文章,每一篇都是评论和鉴赏的提炼,是热爱、分析和历史的糅合,它们让读者以崭新的目光和重燃的热情回味(或者说先睹为快)所评述的影片。伊伯特的影评广泛覆盖各种类型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从电影艺术史上至高无上的经典作品到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娱乐作品。在文章中,罗杰·伊伯特成功地将学者渊博深刻的电影知识、纯美学的判断力与明白晓畅的鉴赏文字融为一体,再配以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部负责人玛丽·科里斯精选的珍贵剧照,使《伟大的电影》成为所有电影爱好者与观众的珍宝库、无可匹敌的观影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