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记得
生活就是一场宴席,弱者多半会饿死。这句话出自 1958 年的一部喜剧电影,名字叫做 [欢乐梅姑]。如今再看女主角当年被奉为神迹的表演,夸张的肢体语言,飞快的语速抑或是变化多端的面部表情,都更接近于对卡通的简单模仿。甚至是对于一部影像艺术而言,[欢乐梅姑] 的舞台感也大于电影感,有失于单调。可是作为一部电影,六十几年的时间,锈蚀了当年最受瞩目的部分,可与此同时,也赋予了其崭新的意义。比如梅姑追求个性独立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自由感,甚至是六十年几年之后,那种享乐阶级的矫揉造作,都没能超出 [欢乐梅姑] 的射程。这是电影的另一重魅力,就像那部被美国西点军校列入教科书去反复研读的 [拯救大兵瑞恩],当年被开头一段抢滩登陆战震惊得目瞪口呆的那些人,许多年后,重新记得了年迈的瑞恩,颤抖着,重回故地,看望当年战友的镜头。绿色的草地上,排列着白色的十字架,如森林般一眼望不到头,已经苍老得站立不稳的瑞恩,望着眼前的十字架,就像看见了十字架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战争的残酷,可以用枪和子弹去表达,也可以用阳光、老人、十字架去表达。有时候,后者的力量更为绵长。同样,在 [教父] 这部电影里,迈克尔接管了家族事务,在处理一件关于拉斯维加斯赌场的事情时,说出了他的父亲在影片开头时说出的那句台词,“我要提出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新一代的教父,在杂草丛生的现实里,露出了他不容置疑的微笑。电影在到底是一件产品还是一部作品,是商业属性大于艺术属性还是艺术属性大于商业属性的争论中,走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就一部电影说一部电影,作品本身的辐射弧度,在当下的时光里,会呈现我们意想不到的光芒。我们也可以利用 100 年这样的时间段,去生成一个参考值,重新比对电影的意义,或许答案会比电影本身更富有戏剧性。在我们已知的标准答案里,一种说法是电影的造梦机能,就像 1941 年的 [马耳他之鹰] 结尾,一个警察问山姆马耳他之鹰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山姆意味深长地回答说,“由造梦的材料做成的”。另一种说法是,电影帮助观看者重新发现人,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被忽略、被漠视的人,在镜头里会显现出远比我们肉眼所见到的更为丰富和鲜活。就像在 1999 年的 [喜剧之王] 里,柳飘飘被打得鼻青脸肿,仍然坚持着对妈咪说,“我不干了,我爱上了一个人”。喜剧,是全世界的第一大观影类型,因为喜剧更能体现电影对于生活的改造能力和抽离功能,对于观看者,在喜剧观看的这两个小时里,重新获得了生活的掌控力。笑,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愉悦,就像 [天使艾米丽] 里说的那样,你永远也不知道有多爱她,除非你发现她和别人在一起。只有将喜剧并列在一种秩序里,我们才会发现,所有的喜剧都是人的艺术。就像动作电影的裂度是建立在独特的动作演员身上一样,喜剧电影对演员的要求,也有着隐秘的规则秘境。还好,总有伟大的艺术家能在现实的芜杂里发现喜剧的忧伤,而我们只需要记得他们。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分享「微信」扫码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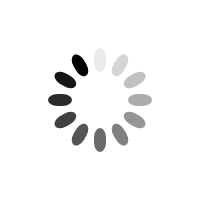
 电子书
电子书看电影(2020年第11期)
本期主要内容《无社恐,不演员本·卫肖》《笑声不断电影喜剧人1OO》《嘴强王者艾伦·索金》《国产动画电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