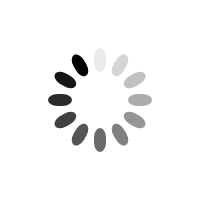《人间词话》是一本毋庸讳言的好书,但是在看到叶先生的讲读之前我对此无感。我跟着叶先生的讲读开始重学宋词,而这本《人间词话七讲》是我重学宋词的一道槛。
曾经细究过,到底应将本书看作 “门槛” 还是 “台阶”。时隔数月,我最终认定这本书在我重学宋词的路上是一道门槛,在读过这本书后,我才算正式走进了宋词背后的大天地 —— 我可不是说能够读懂宋词有多了不起,而是想说,真正读懂了宋词,才能从文学中看到 “唐宋变革” 是如何地发生、元曲如何通过宋词继承了隋唐一代文学并下启明清小说这个脉络。“唐诗不能代表隋唐一代文学” 是我反复阅读唐人笔记、志怪、传奇、小说得出的结论,不过在这本《人间词话七讲》里,读者只需要跟着叶先生讲读,去看懂宋词的真相。
如同《人间词话》是一本简短精练的好书,本书并不是一本补缀之作,而是基于该书的二次创作。叶先生并不是一位译者把王国维的思想从文言翻译成白话,更非直接解读某一两首宋词,她在讲读本书的二次创作中更多地是借用《人间词话》一书重建了王国维与宋词相关的精神世界 —— 她就在书中直接引述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一段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词、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叶先生引述的这一段极其重要,数月前读到此处我没有格外留心,但是最近正值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映,我在回顾时重读这段便条件反射式地想起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后的新文化运动时代。该书上篇发表于 1909 年、下篇发表于 1910 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在 1909 年正好 30 岁而李大钊 20 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党的奠基人是否在当年就读到《人间词话》不得而知,但是当时陈独秀已经在使用浅近文言文为大革命鼓吹,而李大钊已经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已经不可能再是 “旧语文”。王国维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写作《人间词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将西方哲学和文学评论的观点代入对宋词的文学批评,显然不能单纯地看作只是为了怡情悦性。
在我看来,王国维更像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之初主张 “二十年不谈政治”、为国人进行文化启蒙的践行者。只有先把这样的写作背景代入,才能把握到叶先生在讲读《人间词话》中的思想推进节奏,也只有代入了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的思想主旨,才能把握到本书七讲始终在循环推进的 “词之境界” 是为了通过新语文唤醒每个人心中的 “自己”。
关于 “唤醒自己” 这么个命题,用叶先生的观点来说,“因为宋人他们写在诗歌里边的不像写在词里边的真诚”,以及 “正是由于你一心饮酒作乐,正是由于你不必写那些冠冕堂皇的言志的话,所以你的内心松弛下来”,以及 “因为作者脱除了外在的约束跟限制,所以在词里反而常常能够把内心最真诚的本色表现出来”。
不过,单纯地表现最真诚的自己,就合适吗?
这就要用到王国维对于 “境界” 概念的阐发,以及叶先生对 “境界” 概念的校正和补充。确切地说,本书通篇都在借用宋词和词人来完成这个工作,我还概括不了。我唯一能描述的,则是王国维所言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简言之,人人都能通过 “小词” 这种方式呈现、参与和体验到 “境界” 这种比较玄学的东西,只不过各人有各的造化,所能呈现、参与和体验的 “境界” 有高有低罢了。
文人士大夫能搞创作、主动地寻求境界这种精神活动,至于俗人如何参与和体验到境界?
这就要靠杂剧、元曲这些更善于造梦的文学了。其实在创作《人间词话》的同时期,王国维一直在进行中国戏曲研究,1908-1913 年间先后纂写了《曲录》、《戏曲原考》、《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和《古剧脚色考》,这七部著作的写作时间完全覆盖了《人间词话》创作同期。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划时代的《宋元戏曲史》才得以问世。
说点题外话。
我对王国维这般创作历程的理解是,宋词形式和实质均较大程度来自于唐宋大曲的 “无乐 (
yue) 不作”,而元代初期科举废止、文人 “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于是 “词之境界” 变成一条通道,把唐宋大曲和滑稽剧、宋词、宋杂剧、金院本以及南戏合成变形出元曲这种兼具境界和更易普及的形式,使之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中被普及,俗人不仅得以参与和体验,更能培养出自己对于境界的审美能力。对比一下当代的电影艺术,不正是把文学、音乐和美术等艺术融合到一起让大众更易于接受了吗?
这番感悟未必是在阅读《人间词话七讲》这本书时就能有的,但是如果没有遇到这本书,我肯定还依然看不上元曲和元杂剧,现在想来也觉得好笑,人越无知就果然是谁都看不起。
话说回来,叶先生正是王国维笔下的 “解人”,庆幸自己被她牵着跨过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门槛,发现了自己真正兴趣所在。